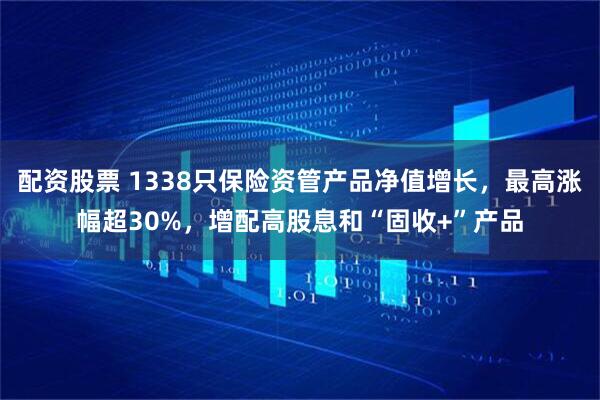1964年1月的一天清晨,泰和县马家洲的雾气尚未散去,几辆吉普车突然在河埠头停稳。村民围拢过去,只见身着灰色呢大衣的曾山快步走进一座瓦房。“发桂同志,我来看你!”他伸出双手。屋里那位鬓发花白、正在烧早饭的农妇愣了几秒,随后眼圈一红——三十年了配资股票,面前这位是当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。
乡亲们听不懂他们口中的称呼,只知道这位大领导很尊敬黄发桂。曾山给她塞上五百元春节补助,又转身对随行干部说:“她曾是省土地部长,按红军干部待遇落实。”一句话,让沉寂多年的往事一下子沸腾。
时间拨回到1928年春,崇贤山谷里杜鹃漫山。15岁的黄发桂原本只想折朵花插在头上,忽然枪声、火光从山下传来。谢云龙领导的暴动捉了恶霸,把粮食分给佃户。有人说:“只有革命,穷人才有饭吃。”这句朴素的道理像种子埋进少女心里。
那年夏天,她加入儿童团,夜里放哨、贴标语,脚板磨出血泡也不说疼。第二年4月,毛泽东率红四军来到兴国。黄发桂与几位女伴天不亮就步行六十里赶到鸡心岭听讲话。“要打倒反动派就得拿起枪。”毛泽东的洪亮声线在人海中炸开,她第一次真切感到革命的重量。
不久,兴国崇贤区苏维埃成立,16岁的黄发桂被推举为区妇委主任,剪辫子、放小脚、识字班,一桩桩新风气在她手上生根。1931年,她又被调任兴国县妇委书记。初到县城,她悄声抹泪,还是遵守组织决定。

1932年,黄发桂随陈毅到宁都巡视。敌机低空扫射,她扑在一名小脚妇女身上,小腿中弹,没等血止就继续疏散群众。这年10月,她被任命为江西省土地部长,兼省政府机关共青团负责人。
1934年初,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。大会选举时,她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同列中央执行委员名单。兴国被誉为“模范县”,她的名字排在第二位。会后,她主动报名去边区——登贤县副主席兼妇女部长的任命书很快下来。
登贤地处白区夹缝,夜里枪声不绝,白天发动群众支前。一次夜行途中,她被两名敌兵围住,情急之下匕首刺倒对方,翻身遁入密林。第五次“围剿”后,游击队转入深山。弹尽粮绝,队伍被迫分散。黄发桂改扮村妇,混出封锁线,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。
此后十余年,她撑船、种田、乞讨,甚至改嫁船工邓百发。每到集镇,她都会悄悄张望,希望出现熟识的臂章或暗号。1938年,一名叫钟平的老同志终于在赣江边找到她。可形势动荡,他们一次次转移,几度险些被叛徒出卖。泰和监狱的铁镣、竹签并没撬开她的嘴,凭着黄姓族长担保才侥幸脱身。
抗战胜利后,她回到马家洲,挑河泥、织草席,抚养三个女儿。解放后的喜讯传来,她依旧没有上门报功:“1934年中央离开苏区时把江西托付给我们,可我们没守住。”倔强与自责让她闭口不提过去。
1950年,曾山向太和县政府写信查人,几番波折才摸清她的落脚点。陈毅随后邀她去上海工作,黄发桂考虑家累,婉拒。组织没勉强,只是将她安排到土改工作团,随后又批准她回乡做妇女干事。

1964年的探访,让许多后辈第一次知道自家乡邻曾端坐中央礼堂。可黄发桂依然粗布衣、草鞋底。省民政厅每月补助,她常偷偷塞给更困难的人。
1981年9月,她被诊断为癌症,家里凑不出住院费。女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谢象晃写信,批示当天批下:全部费用公家承担。住进南昌医院时,她只带了一只旧箱子,里面放着那枚已经褪色的第二次苏大代表证。
临终前,她叮嘱子女“心里要装着别人,别只想着自己”。传奇没有隆重谢幕,她的墓碑简简单单,只刻姓名、生卒和四个字——“江西苏维埃”。
配先查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股票 12月23日华兴转债下跌0.12%,转股溢价率25.42%
- 下一篇:没有了